舒倩《漁歌》
晚飯后,我下樓沿著圭塘河散步,恰巧遇上了饒姨,我們便結伴沿著河岸慢行。晚風輕拂,河水漣漪,我們走得忘記了時間,聊得盡興,從她的娓娓講述中,我聽到了一段與洞庭湖緊密相連半生的故事。
饒姨名叫饒鳳群,今年56歲,來自常德市漢壽縣巖汪湖鎮。90年代起,她和丈夫一起打魚,整整打了二十八年。“我爺爺曾說,如今鎮上人們居住的地方,很久以前還是一片汪洋。”她望著波光粼粼的河面,輕輕說道。
在饒姨的記憶里,她和丈夫擁有的三條船便組成一個流動的家:一條是生活船,吃住都在上面;一條是帶有魚倉的活水船;還有一條小筏子,大船過不去的水汊,就得靠它進去清理障礙。
“每次出湖,短則七天,長則半個月,我們的路線從西洞庭湖一直漂到東洞庭湖。”饒姨回憶,90年代那會兒,航道很窄,碰上從岳陽跑常德的客運船,交匯時特別危險。大船駛過掀起的尾浪,輕易就能把小漁船打翻。“如今啊,要是不漲水,那航道感覺比90年代還要窄哩。”她嘆了口氣。
這二十八年的水上歲月,生活遵循洞庭湖的節律。“春天是捕魚的好時節,到了八月,魚就難捕了。于是九月便開船去岳陽挖泥蒿,再運回常德的批發市場售賣。等第二年過了春節,到驚蟄節氣,便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捕魚。”
兩口子在湖上討生活,風險如影隨形。她曾一腳踩空掉進湖里,萬幸被丈夫眼疾手快地救了上來。那時候,他們全靠收音機來獲取天氣消息。一次,得知有大風沒敢下湖,兩天后風停了,卻發現自家的船不見了——原來是被大風刮進了遠處的蘆葦蕩。而另一對相熟的夫妻就沒這么幸運了,他們下湖時遭遇風浪翻了船,丈夫僥幸抓住浮木活了下來,妻子卻永遠沉在了湖底。“二十多年了,那男的再未娶。”現在想起這段往事,饒姨還是會不由的傷感。
盡管危險,但那也是她最懷念的日子。饒姨說,“在水上,自由自在的。”
2019年,漁民上岸政策落地,她家的漁船、漁具也被統一回收。于是夫妻倆去浙江打工,在工廠里干活需要夜里倒班,他們常常要端著幾十斤重的模具,將飾品用高溫火爐融化后倒入模具,再放進水里冷卻。“實在不適應那種生活,”她搖搖頭,“還是回了老家。”休息了一段時間后,他們開始去別人承包的魚塘里捕魚,然后拿到市場去賣,收益和塘主對半分,一直干到現在。
我想起有政策要求將人工魚塘填埋,改種水稻。于是問她,如果以后連魚塘也不能捕魚了,該怎么辦?她沉默了一會兒,望著遠處說:“沒辦法了,年紀大了,出去打工也沒人要。我除了打魚,什么也不會。”
除了在魚塘捕魚,饒姨還做起了“中介”的活計:幫一些釣魚愛好者把漁獲拿到市場代賣,賺點差價。最高一斤賺三塊,最低五毛。這差價里還得包括幫客戶處理魚的費用,需要殺魚、腌魚、放到冰柜冷藏什么的。“都是掙點辛苦錢。”饒姨下意識地搓了搓手,我看向她的雙手,因為常年在湖上,風濕很重,手指已經有些變形了。
說起洞庭湖,饒姨的話里透著一股復雜的感情,他們其實也早就察覺到湖的變化。在沒上岸之前,她與丈夫將漁網放進湖里,第二天必須趕緊收回來,一旦遲了,網具就被厚厚的淤泥埋住。她告訴我,她家里至今還有一百多張網,就這樣永遠留在了湖底的淤泥里,怎么也撈不回來。
“不只是淤泥,以前沿岸泊船,能停長長的一串,”她比畫著,“現在那些泊船的地方,好多都成了陸地。水是真的變少了。”聽到她說這些,我深以為然。昔日浩瀚的湖面被洲灘分割、填充,這正是湖面萎縮的直接體現。
上岸后,夫妻倆有時會去西洞庭湖保護協會做志愿者,回到熟悉的洞庭湖,巡護、清理垃圾。我問她,當初怎么會想到去做志愿者?她說,一開始,是濕地保護協會的劉克歡會長叫上他們夫妻倆,覺得反正閑著也是閑著,就去吧。到了湖里才發現,垃圾越撿越多,好像永遠都撿不完,半天工夫就能裝滿兩輛垃圾車。每一次退潮后,露出的垃圾更是觸目驚心。
后來,這倒慢慢成了習慣。會長一招呼,他們就一起去。饒姨告訴我,不少像她一樣的漁民都從捕撈者變成了志愿者,昔日爭漁場的老對手,如今并肩撿垃圾,倒像是一種新的“聚會”。除了撿垃圾,他們也到漢壽縣發環保宣傳冊,或是聽一聽關于生物多樣性的科普講座。
“我對洞庭湖,那是真有感情的。”夜色漸深,饒姨的語氣格外誠懇,“它養了我們這么多年。我們在湖上生活,向它要吃的,它就給吃的。現在知道它‘受傷’了,也該是我們去幫幫它的時候了。”
河風吹來,帶著初秋的涼意。我看著這位從大風大浪里走出來的漁民,如今在城市的河畔平靜地講述過往,心中充滿敬意。
饒姨的經歷,可以算是我國23萬退捕漁民的一個縮影。截至2022年末,中央和地方累計投入270億元用于長江禁漁退捕漁民安置。無數的饒姨們雖然懷念在湖上“西風吹老洞庭波,滿船清夢壓星河”的日子,卻更清醒于“湖累了,該歇歇了”的現實。據我所知,漢壽西洞庭湖濕地保護協會有四百多名志愿者,其中,有七成是退捕漁民。如今,他們成了西洞庭湖生態保護的中堅力量,用最熟悉的方式,反哺那片曾經索取多年的湖水。
他們讓我更加意識到,人與自然的命題,從來都不是征服或索取,而是共生與守護的和諧關系。
饒姨的故事,是一首關于犧牲、轉型與希望的漁歌,歌詞里有艱辛,有危險,有無奈,但最終,卻匯成了一曲深情的守護之歌。這首歌隨著志愿者的腳步,在西洞庭湖的晨霧與暮色間,一聲聲,傳得很遠、很遠。
作者簡介:
舒倩,湖南省作協會員,文學創作三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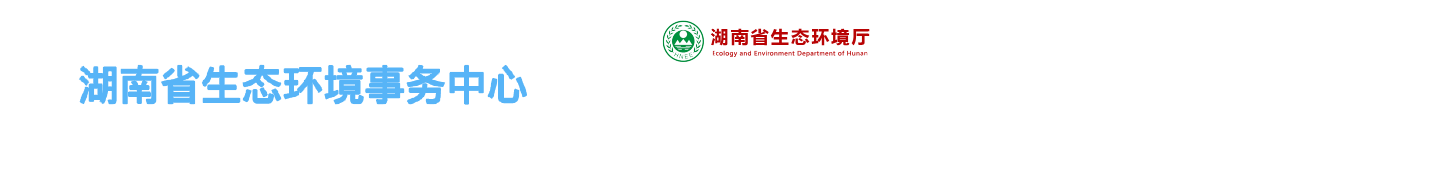


 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964號
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964號